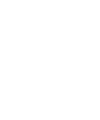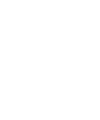出现又离开 - 37.余波
向晗忘不了离开安州那天。她在后视镜里看见季绍明的车远远跟着,原先保持距离,上高架桥逐渐疏远,像被她留在呈螺旋形态的回忆原点,停滞在那里,最终消失不见。她以为他放弃时,在高铁站的进站口,玻璃的倒影里又出现了他。他像从水里捞出来,发茬的汗珠在阳光下闪光,脖领一圈汗湿。
向晗回身,戴着墨镜季绍明也知道在瞪他,他转头向车子停靠的方向走几步,向晗扭头接着排队,他又转头走近她,向晗再回身瞪他,他掩耳盗铃看地,装无事发生。
她知道他在等人脸核验,她会摘下墨镜。
把戏玩过四遍后,季绍明已走到她面前了,她迈出队伍两步,压低声音说:“你有完没完!”
他觉得生气令这张脸更有活力了,越看越喜欢,眼珠子扒在向晗脸上,想把她的五官拓印在脑子里。
以前怎么没看出他是个无赖,她像赶狗一样,猛跺地一脚,吼道:“滚!”
季绍明并未被吓退,也不强摘墨镜,嘴唇抿着,黑亮的眼眸度量她,他不曾有她的一张相片,他就自己来造。
镜片反射的太阳光灼白,额际的汗水渗湿帽子内衬,凉凉地贴在她脑门上,暴晒之下,向晗忍无可忍。她想到眼下的伤疤因何而来,她就愤怒,她要让他的身体也长出疤痕,难以掩盖的疤痕。
短袖下方的大臂,一口咬住。汗咸,血腥,虎牙感受到皮肤破碎。季绍明更疯,竟觉得快乐,爱情的疼好过没有,他低头说:“我爱你。”
疼痛停止了,向晗顶着歪斜的棒球帽,冲向人工通道,工作人员看眼她的身份证,放她进候车厅。她大脑里一遍遍回放那句“我爱你”,和季绍明哀戚的语气。
梓玥叫她男朋友滚,带着向晗去北方避暑,在阿那亚时,向晗躺在海景房的大床上发呆,露天音乐会、海边日出统统不感兴趣。她下狠心要去安州分手,梓玥一愣,说齐星宇在杭州啊,他回去啦?向晗坦白道是季绍明。
她狂摇向晗肩膀说,季绍明,你没搞错吧。向晗瘫在床上不动弹,梓玥说早知道是他,我扛火车带你跑,老男人能玩死你。她坐起看梓玥一眼,梓玥说完了,你还不舍得我说他。
梓玥也没机会唠叨她太久,广东老家那边的银行喊她入职,她有濒死感那天,其实只在天盛加班到八点钟,又去健身房跑步,在更衣室里剧烈胸痛。向晗拥抱她,耳朵贴在她嘭嘭跳的心脏上,她清楚审计这行是青春饭,高强度熬夜对身体的损伤不可逆,她的健康也有问题,过去灌太多咖啡,现在喝瓶能量饮料就手抖、心悸。
她闻梓玥身上的棉花籽香味,一如八年前军训初见她时,宁静的夏天,她们居然都逼近过死亡。眼泪从眼角划向发际,她牵梓玥的手,说我想你了怎么办。海风吹得白窗帘摇摆,梓玥说那就回家啊。她蹙眉不解,梓玥眨下眼睛说,回你广东的家。
整个七月像做梦,上旬甜蜜,中旬惨烈,下旬荒凉。八月份向晗终于回杭州上班,陈敏说她是面黄肌瘦的难民。向晗也想不到得过“大胃王”称号的她,有吃不下饭的一天。她早上在茶水间冲咖啡,黑眼圈像两朵泡发的黑木耳,陈敏制止她摁饮水机的手,说梓玥出事了,你别再有个好歹。
向晗虚弱地笑笑,季绍明的失眠并没有传染给她,她是神经衰弱。入睡不是难事,从三点钟开始,她每隔一个小时醒一次,看看手机时间又钻进被窝,睡得极浅,直到预定的闹钟响。
梦里她永远在那个雨夜,声控灯明灭的楼道里和父亲互殴,有时她指甲刺进父亲的血肉里,有时她用一条丝巾勒得他翻白眼,但无一例外都是弑父。
陈敏不知内情,见她憔悴,满脸匪夷所思道:“为季绍明?”
向晗嗤笑:“他哪有这么大的魅力。”
良久,她又说:“……也有点关系吧,和他的事被家里知道了,起了冲突。”
陈敏把相熟的心理咨询师推给她,休息日她在写字楼下喝光一杯薄荷水,牙床滋滋凉,转身进楼去工作室。过程并不治愈,她对着陌生人大吐苦水,依然无法哭出,唯独房间的那把胎椅柔软舒适,真像母亲的子宫包裹她。咨询师无非说些接受自己、自我调节的话,建议向晗布置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有助于深度睡眠。
那就好办多了,以前她点香薰蜡烛助眠,现在稀释84消毒液拖地,往枕头被子上喷酒精,气味刺激到她想干呕,可是没有用,她双臂圈住自己,模仿被拥抱的姿态。
八月份安州的气温下降,有时晚上不开空调也能睡觉,北方就是这样,凉得快。季希趴在窗边看她爸在院里下象棋,一片心形的杨树叶落在窗台上,她想夏天快结束了,下几场冷雨秋天也会过去,十一假期一过,安州就正式进入漫长乏味的冬季,一年其实快得很。
她听见楼下的大爷问他胳膊怎么回事,季绍明捂着结痂的伤口,抬手拱卒说,做梦醒来就这样了。大爷问噩梦啊,还带咬人的,季绍明说美梦,不疼不清醒。
暑假的实践作业是“夏日卫生大作战”,家里被季绍明打扫得干干净净,窗户拿旧报纸擦得锃亮,连水迹都没有,季希只好去韩文博家完成作业。邹颖不爱干家务,韩文博懒得干家务,可有季希忙的,她又是洗空调滤网,又是用鸡毛掸子除尘,带着他俩也干起活。
录完作业的视频,韩文博切西瓜三个人分,邹颖接过果盘,啐他道:“还骗我洗滤网了,吹一夏天脏风。”
“权当增强免疫力了。”韩文博痞笑着拿块西瓜,扭头问希希:“你爸最近咋样?”
韩文博知道他和向晗分了,分手那天他撞见过他,他下车胳膊淌血,上衣被汗水浸湿成深色,走路直打飘。韩文博看车里根本没开空调,张嘴想骂他,见他面如死灰的样子,也觉得可怜,抿抿唇什么都没说。
希希说她爸现在四点半就出门晨跑,韩文博冷笑一声,想他是夜里都没睡吧。
她又说爸爸开始养鱼,红红的小金鱼,还买了好多彩石子和水草。每次只买一条,养两三天死了再买。
“我说鱼是太孤独了才死的,我爸不接我茬,说他只养一条鱼。他养的水仙也死了,晚上睡觉前,他把当天死的鱼埋在水仙花盆里,第二天早起去花鸟市场又买。”
邹颖仿佛能看见季绍明握小铲子刨土埋鱼的情景,她和韩文博看彼此一眼,放下瓜皮,喃喃道:“水仙已乘鲤鱼去。”
季希托腮想这就是分手的滋味吗,两人正伤感呢,韩文博在旁边嘎嘎乐,说:“真逗,水仙骑鱼上!哈哈哈!”
希希怜悯地看向邹颖,邹颖拍拍她头说:“好好学习多重要。”
“小婶,平时交流很累吧。”
韩文博脸垮了,闷头啃西瓜嘀咕:“说得酸不溜秋,你爸就是老房子着火,把自己烧没了。”
半夜季希偷摸去餐厅拿零食,开门缝看外面,独独一盏吊灯亮着,季绍明半张脸暗在阴影里,挥网捞出死鱼,面对坛子造型的花盆,自言自语说放不下了。
他埋完鱼,用铲子背面拍拍土,俯身抽出餐桌下的锡纸,坐在小马扎上迭金银元宝,一时间钟表的滴答声和折锡纸的沙沙声交错,在季希的神经末梢跳踢踏舞,餐厅的窗户吹来一阵阴风,正好对着她的房间,季希起鸡皮疙瘩,看不清父亲此时的表情,只觉得像个机器人,后脊背发凉。
恍然听见他说一句:“不睡觉就过来干活儿。”
她迅速关门,背靠门板喘气,方想起明天是农历七月半。
多年的规矩是季希和刘意可先去祭拜,她们是血亲,季绍明错开晚点去。安州城的陵园只有一座,依山而建,他停妥车子,进陵园时特意去大门口水池边,拧开水龙头给买的花洒点水,大朵的球菊怒放。他捧着花,挎着一竹篮的金银元宝,爬阶梯上到高处的墓穴位。刘意可她们已洗刷干净墓碑,水果和酒供奉着,早晨新下过雨,山里阴凉入骨,他拉上冲锋衣的拉链,凝视刘志光的笑容。
他站着说了许久,说他没把庄涛拉下台,说他没用被辞退了,又说您别担心,我接的有私活儿,养希希没问题。提到女儿他脸上露出点笑,您看见了吧,她个子和意可一般高了,是个小大人,道理比我们还清楚,我都快管不住她了。
他放下菊花,调整多次花的位置,确保每一朵花都是舒展的,又去搬公用的铁盆,烧金银元宝。他借盆里的火点根烟,比着墓碑的中轴线,横放在地上,再给自己点一支。说他爸现在对他都有意见,嫌他们父子不亲。
“那确实比不上我跟您。”他弹弹烟灰笑说。
半山腰的竹子被压弯了腰,季绍明想到少年的自己。他说他有一段时间非常恨父亲,油然而生,时隔多年都确切的恨。好像是在击打中,他跪地双手向上时产生了恨意。父亲要求他争第一的心有多强烈,他的恨就有多恶毒。
直到他十六岁,没考上清北,也不接受复读,毅然去北京上学,那恨才像琴弦“嘎”一声断了。
他说他是季学军的败绩,清北班名师的耻辱。雨水落下,滴在墓碑上,像刘志光在哭,他伸手抹去水滴,说师傅您不用难过,我现在不这么想了。
他坐在地上,举起右手说,您还记得这儿吗。他的手是干活的手,十指修长却骨节粗大,肤色暗淡,虎口处有一公分的淡疤。
第一天上班,他毁坏价值不菲的刀具,手割破缝了三针,以为就此打道回府,刘志光却说人没事就好,刀具他有法子修。他莽撞地摸索,执拗地用书本上的死知识,刘志光好像从未生过气,笑呵呵地等他撞了南墙,再告诉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手把手教他该如何处理。他永远不必担心犯错,因为错误反倒令他收获更多知识。
天是灰的,漫山的墓碑也是灰的,墓与墓之间的矮松成了唯一绿色的点缀。他坐在地上,面向山下,又点一支烟,悠悠说,今年他遇到了第二个让他感到无比轻松的人,他们无限接近幸福了,可他觉得不能那么做。
他说他有段时间分不清对她是冲动还是爱,他们不见面,可他一想到她心底就是甘甜的,继而是惊恐和绝望,他的脑子和身体朝两个方向发展,扭曲他成一个痛苦的变形人。
“以前不是没想过再找,我总觉得跟谁过都一样,没意思。她来了,我才有点盼头。”
季绍明掐灭烟头,像说话又像宣誓地说,他会安静地等待爱情退潮,他有的是时间耗,哪怕用一辈子。
他甘之如饴。
--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