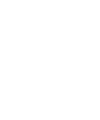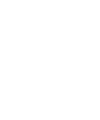杀尽江南百万兵【1v1 元末明初】 - 救不及
此言既出,如一盆数九寒冰兜头而下,将王莲芳浇了个透底。
他惶惶然站起身,愣怔着与孟开平对上眼,很快余光又望见一旁半卧着的伤患,这才明白原是那通传的小兵传误了消息。
“孟、孟元帅……”王莲芳结结巴巴,字不成句道:“实在是、是老夫莽撞了……”
男人沉着眉目,闻言冷笑了一声,不置可否。
犹记当日他还曾告诫过王莲芳,记得从今往后夹起尾巴做人,莫要再出现在他面前。可这才过去一年多,老头子竟又上赶着来找死,恐怕只因自己先前太过手软,没教他好生长个记性。
眼前那杆红缨长枪的枪头闪着敛不住的锋锐寒芒,王莲芳两股战战几欲先走,但他终究还是忍住了。为了暂避锋芒,他突然心生一计,状若凛然道:“闻有伤重,岂能坐视不理?老夫既受容夫人重托,又身处应天,自然义不容辞。救人要紧,还请元帅您稍让两步才好……”
“哦?”
孟开平饶有兴味一挑眉,出乎意料的,他竟也没多为难王莲芳,反倒大度颔首示意他上前医治。隐隐的血腥气弥漫在厅中,王莲芳擦了擦额间的冷汗,定神上前一瞧,心境却急转直下凉了一半——
暗箭难防,穿目而去,这只眼定然保不住了。
其实伤者他也识得,正是孟元帅声旁常跟着的副将袁复。此人倒是个硬汉子,尽管伤处血流不止,他却始终咬着牙一声不吭,反教观者替他揪心捏汗。王莲芳难免暗暗唏嘘道,不幸失了只眼,往后在战场上可就更难活命了。
“回程遇袭,先止血罢。”
不知何时,孟开平也迈步过来,同王莲芳简略吩咐道:“稍后你再同另几位大夫商议处置,不拘如何,保命要紧。”
王莲芳也不知孟开平是太放心他的医术还是早知袁复的眼根本保不住,乍瞧上去,他并不是十分忧心。交代完这些,他甚至都没多宽慰袁复半句,面色平淡得几乎有些飘忽,不知在另外思量些什么。
王莲芳心里嘀咕不断,视线也不自觉在孟开平身上梭巡,神色紧绷间流露而出的除了惧怕还有纳罕。孟开平自然注意到了这些,然而,他却只淡淡回道:“你从医多年,可我见过的死人远比你多,死状惨烈者更是不计其数。这种小伤不过皮毛罢了。”
小伤?王莲芳不由咋舌。这箭若再稍稍偏离半寸,便足以将脑袋射穿了,当真唯有活阎王才见怪不怪。
他正欲反驳两句公道话,没想到那袁复尚未疼昏过去,闻了上峰此言,竟也咧嘴笑着附和道:“大夫,你尽管下手治,咱老袁吃得起痛!最好使些猛药,莫要耽误过几日行军才好!”
瞧见他嬉笑间随性洒脱,全然不怕日后成了个半瞎,王莲芳简直恨得牙根痒痒。他现下总算明白了,怜悯这群亡命之徒根本就是白费功夫,他们自个儿都不拿身子当回事,他还多余开口作甚!
很快,另几位大夫也都围拢了过来,七嘴八舌商量着如何处置伤口、开方配药。孟开平晓得这会儿用不着他了,便默默退了出去。他本想去寻郭英议事,结果刚迈出厅门,远远便望见大公子齐暄朝他跑来。
“孟叔!”
小小少年方才下学,一听说孟开平回来了,便飞也似地奔了过来急着见他。孟开平闻声,眼含笑意,快步上前稳稳将他接进怀中。
“倒是重了不少。”他用臂弯掂量了几下,随后又俯声弯腰将他放在地上,仔细打量了一番,笑语道:“才多久不见,竟长高这许多,往后怕是要越过你爹去了。”
“孟叔,我定会高过你的!”齐暄伸出小手比量了一下,胸有成竹道:“爹爹要我随黄将军习练枪法,认他作师父。黄将军说,会使长枪的就没有矮个子,你说是么?”
“呵呵,那是自然。”孟开平拍了拍他的肩,极温和道:“好好同你师父练,读文章要紧,身板儿更要紧。黄珏的枪法不赖,你若能学到五分,便也称得上是‘文武双全’了。”
齐暄认真点点头,其实他更想跟着孟开平习武,无奈孟开平长久在外争战,无暇分身。两人立在庭院中聊了些应天近来发生的趣事,很快,齐暄又想起另一桩喜讯,于是迫不及待告予他知:“对了,孟叔,我有四弟了!阿娘此番生产颇为凶险,多亏了王太医一众人等尽心尽力,方才能化险为夷……听说他是沉将军从徽州请来的,阿娘还赞他慧眼识人呢。”
“爹爹准我为四弟取名,我取了‘晔’字。《广雅》中有言,晔者,明也。二弟与叁弟如今随着宋先生开蒙入学,心思并不在校场之上。但爹爹许诺,往后待四弟长成,便教他多读兵法、多问军务,好做我的左膀右臂!”
王太医……又是他。
孟开平抿唇,他仰头看了看天上大好的日光,莫名觉得那光太过刺目。
初夏午后,暖意融融,可他的魂却似丢在了连绵潮湿的雨幕中,再也寻不回来了。明明是旧岁叁月的痛楚,他至今仍然恍惚觉得一切只在昨日。他不敢面对,又无法抹去与她相关的所有人与事,所以只能逃避着麻痹自己。
其实当日抓到王莲芳,他本想杀之以泄愤的。可偏偏那个女人太懂得如何拿捏他了,她早将一切都算准了。
“……我愿天地炉,先从冻馁均。自然六合内,少闻贫病人。”
“……元帅您少时也是深知贫病之苦的,师小姐她力主修建养济院与善药局便是为此。今日,没了我这一风烛残年的老叟并不可怜,只可怜天下稚子心。我死后,还望元帅您莫要再迁怒于旁人,更要延续师小姐的仁政之德。须知得民心者,必得天下。”
孟开平知道王莲芳这套说辞都是师杭教给他的,可知道又如何?他对此明明白白,却无能为力。
孟开平无法形容当时的滋味,仿佛心中疯狂蔓延燃烧的烈火终于烧至了尽头。天边的斜风细雨柔柔压来,不懈地与之抵抗纠缠,最终,心原上的苍茫大地余烬成灰,他再也提不起分毫杀意。
直到听了这番话,他才恍然发觉原来师杭是那么地了解他。他向来以为自己对她了如指掌,可事实竟是,他根本看不透她,反倒是师杭已经将他看得清楚见底——
她了解他的身世与经历,承受他的愤恨与怨怼,明白他的压抑与不甘。多可笑啊。他还愚蠢地以为掌握权力就可以摆脱卑劣低贱、任人摆布的过往,其实不论他闯得再远,都没有闯过多年前母亲病逝的那个秋日黄昏。
那时,夕阳的光越过窗棂,投映在孟开平瘦窄孱弱的背上,一大片挥之不去的阴影牢牢拢住了他。年幼无知的他以为那仅仅只是一瞬,没想到那片阴影往后竟足足覆沉了他十六年人生。
“……孟叔?”
齐暄的呼喊使得孟开平收回思绪,不知何时,刘基也来到了二人身侧。他瞧了眼孟开平的神色,知晓后者心不在此,思忖片刻后便同齐暄熟络道:“大公子,明日便是端午了。难得佳节,不如明日同在下去玄武湖畔游玩一番,与民共庆如何?”
“甚好甚好!”齐暄毕竟年岁尚小,早盼着塾中休沐了,闻言岂有不应之理:“爹娘未必得空,有刘先生您一道前往,他们也定然放心!”
“那咱们便如此说定了。”刘基抚了抚长髯,笑眯眯道:“不过先得告知宋濂才好,你若瞒着他出去撒野,节后说不准还要挨板子。”
宋濂一贯是个严师,齐暄听了,立时询道:“那刘先生可否与我一道?”
刘基呵呵一笑,自然应下。
于是顺理成章地,齐暄与孟开平依依告别,还许诺过两日再去府上寻他。刘基也将离去,然而临走前却朝孟开平拱手道:“元帅交予在下的文集已然编好大半了,待元帅下回返京,应当便可见到成稿。至于元帅挂念的那人……”
他顿了顿,意有所指道:“王太医急着回徽州,最多再于应天停留十余日。元帅日后怕是难见他了,若有言,还是早些交代为好。”
说罢,刘基又是一礼,潇洒去也。
孟开平素来不喜跟如此曲折宛转之人打交道,但刘基所言,却当真恰好戳中了他的心思。他扯了扯唇角,复又从院中绕回厅内,只见袁复的伤处已然包扎好了,而王莲芳正絮絮叮嘱他些什么。
王莲芳这厢劳神劳力半晌,好容易松泛下来,侧首却见那活阎王竟去又折返,正不远不近地盯着他,当即吓出一身冷汗。
“元帅还有何吩咐?”他小心翼翼,犹疑问道。
孟开平先是向袁复示意,随后转向王莲芳道:“既然无事了,不知王太医可愿赏脸一叙?”
有什么好叙的,多半是同他算旧账罢?
思及此,王莲芳立时就想回绝,然而孟开平却幽幽继续道:“若是不愿,便是瞧不上我了?”
“……”
这下王莲芳还能说什么呢?他别无选择,只能认命似地提起药匣跟着孟开平去了。他原以为孟开平要领他去虎穴狼巢,没想到这人兜来绕去竟绕去了秦淮河附近的热闹街市,而后又在小巷拐角寻了家馄饨摊子落座。
自古以来,十里秦淮长盛不衰。河岸两边的好去处不计其数,这人却连酒楼都舍不得请他去,真是抠死得了……王莲芳暗自腹诽,因拿不准这家伙要叙什么旧,干脆先在背地里痛快骂了孟开平八百回。直到小二将两大碗热气腾腾、葱香四溢的鲜肉馄饨端了上来,他的怨气才被骤然截断。
“尝尝罢。”
此刻,孟开平一身朴素长衫,挽袖替他递了双筷子,倒真似小友邀约忘年交一般客气道:“好酒不怕巷子深,佳肴岂嫌桌案陋?这摊子虽不起眼,却传了叁代人了。论味道,绝不逊于那烟雨楼叁十文一碗的‘金馄饨’。”
烟雨楼之味美价贵,王莲芳早有耳闻,于是他便顺着孟开平的话接过筷子尝了一口,没想到果真极好吃。他年纪大了,入口不喜过于荤腥,用这个刚好。
“哟,孟公子,您倒许久不来了!”一旁的小二这会儿突然凑了上来,极热情道:“方才光顾着抹桌子,竟没瞧见您!怎么,今儿是带令尊来……”
小儿细细打量了几眼王莲芳的年纪相貌,如此猜测,也算是情理之中。
“哎哎哎,不不不!”
结果王莲芳听了,连忙摇头摆手,差点没被吓得连凳子都坐不稳了。天地良心!他岂敢做这位的爹!孟开平的爹怕是坟头草都有叁尺高了罢?
然而孟开平却并不当回事,仍云淡风轻道:“如今是你看摊子了,你阿爷与你爹呢?”
“不过看几日罢了,我爹可放不下心。前些时候晴一时阴一时的,这不,老头子起早贪黑的,晨间风一吹便病倒了。”小二叹了口气,无奈道:“至于我阿爷,确是年纪大了,实在干不动了……不过他老人家可记着您呢!昨儿还说,若再见您来,千万不能收您的钱,您瞧我这儿没眼力见的!”
说到这儿,小二赶忙一拍脑门,转身就要去屉柜里头摸钱出来还给他俩。孟开平立时站起身阻拦道:“莫要如此,你若这般,往后我也不敢再来了。”
“哎呀,这是说的哪里话……”他人高马大挡在面前,小二走也走不开、绕也绕不过,焦心道:“您好心出了五贯钞,既解了小店的燃眉之急,又不要利钱,咱们怎么好再挣您的呢?如今家中欠下的账都已平了,再过些时日,抵出去的店面便也能收回了。小的妻女皆平安无恙,这都是多亏了您搭救的功劳!”
说着,小二又转向满脸困惑的王莲芳,千恩万谢解释道:“老先生,孟公子可是个大善人啊!去岁春夏之交,我妻女不幸染了疫症,孟公子听闻后没有二话便遣了大夫来,连诊金与药钱都替咱付了。你说说,有几多富贵儿郎似这般好心肠?”
五贯至正交钞,那便是足足五千文了。王莲芳没想到孟开平竟还是个乐善好施者,虽说这些钱于他约莫是九牛一毛,可最最难得的却是此人尚未泯灭其良知,倒也算不上十恶不赦了。
此来应天,这还是王莲芳头一回外出闲逛。乱世当前,天下满目疮痍,除大都外,不知能有几处安稳之城?应天府辖虽不如从前的金陵奢靡醉人,但入目之处皆是生机昂然之气象。路无乞者,家有余粮,法度严明,红巾军在此地的政绩可见一斑。
因有客来,小二再叁谢过后便另去招呼了。这会儿并无旁人,又在红巾军的地盘上,王莲芳望着面前年轻男人英气勃勃的面旁,突然出言道:“听闻齐丞相有意置宝源局铸币,名曰大中通宝,此举,莫不是要称帝?”
弃元币而另铸,唯有一方霸主才敢为之。闻言,孟开平显然怔了一瞬,但很快他又弯起了眉目,不紧不慢道:“这话怎么说?咱们尊的是小明王,用的是大宋的龙凤年号,丞相他必无此意。”
眼下无此意,并不代表将来无此意。韩林儿、刘福通等人长据中原,纵兵抗元,遮蔽江淮近十年。此消彼长间,韩部已显颓势,反倒是应天府这片广揽英才,士气可观。王莲芳不敢直言齐元兴之势大类于曹丕篡权,但他直觉在不远的将来恐怕真有人会颠覆大元。这个人可能是韩林儿,可能是陈友谅,可能是张士诚,自然也有可能是齐元兴。
一碗馄饨用罢,两人间并未再说什么,但王莲芳心中已是百转千回。他活过了一个甲子,往后不知还能活几年,可他的儿孙如今也都在徽州,他不能不为他们打算。
“……无方可疗相思病,有药难医薄幸心。”
将要分别时,王莲芳终于先一步开口道:“元帅既见惯了生死,便该晓得这世上之事大多是强求不来的,但也总有些事,是人力所能及的。江水无情人有情,听闻您并未找见师小姐的尸身,那您可曾想过,或许她并未丧命于江中呢?”
孟开平原本挥了挥手欲走,结果听见这话,果然定在了原地。
“那本《露华集》老夫也瞧了,小姐她果然好文才,便是诔文也写得出气度。可细细想来,若是当真打定主意赴死,字句间又怎会甚少表露愁怨之情?尤其是去岁二月那几首,气象万千,读之竟有柳暗花明之妙韵。心存死志者绝无可能写出这些。”
“再有一桩,其实当日那蒙汗药,并非是老夫开的方子。”
王莲芳不顾孟开平惊异的神情,话锋一转继续道:“师小姐从未向老夫讨要过这物什,便是她要,那么大剂量足以闷杀数人,老夫也绝不会给。至于外头的医馆与大夫,恐怕更没人敢给,唯有些走南闯北的江湖下九流,抑或是山头势力才敢。”
孟开平确实没查出师杭究竟是从何处弄来的蒙汗药。那药几乎放倒了厩中大半马匹,当日他审问王莲芳正在气头上,王莲芳也无暇解释,于是一来二去就将这桩罪扣在了后者头上。现下再提,的确疑点重重。
他猜测过她很可能没死,但她决然的选择也伤透了他。孟开平想,便是师杭还活着,也必定藏在一个极难探寻之地。他总不能放下手头的一切胡乱去碰运气,于是只能走到哪儿便着人打听到哪儿,另外又在师杭可能回返的旧地都布置了人手,一旦发现些微踪迹便会报于他。
丞相府议事厅内,孟开平翻阅着近年来有关徽州苗寨的卷宗,越看越眉头紧锁。
与王莲芳相谈后,他思量了许久,笃定唯一的疏忽便在师杭那一回离奇失踪上。她曾说是北雁寨的人私自掳了她去,后来许是慑于红巾军报复,当家的便又主张将她放归。那时,孟开平舍不得她受了苦,本想着上门找北雁寨好生算账。没想到第二日,几颗血淋淋的人头便被送到了元帅府上。
而与此一同被送来的,还有一封北雁寨当家的亲笔所书的告罪信。
他们诚心乞和,齐元兴的命令也是莫要擅动苗寨,可孟开平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直到后来不知哪一日,他偶然听闻北雁寨与对头因分家结仇,对方率兵攻寨,正打得热火朝天。于是孟开平干脆趁此时机横插一脚,为北雁寨的覆灭掩了一抔黄土,狠狠出了口恶气。
记得当日攻寨的那一方,名为南雁寨,寨主少见是个女人……
“你这腰上的伤,便是华佗再世怕也难治了。”
不知何时,郭英来到他声旁,忍不住提醒道:“什么卷宗如此要紧?都看了两刻钟了。”
大夫嘱他静养,可若不探明此事,他的心绪如何能静?孟开平闻声阖上书册,转而问道:“事情办完了?”
郭英颔首,落座答道:“我在罗绸巷赁了叁间屋子,杭家人流亡许久,拢共也就剩下二十余口人,够他们住了。”
“多谢。”孟开平笑了笑,真挚谢道:“劳烦你许多,上回谢家姑娘的事也多亏了郭夫人从中牵线,否则我可没法子在丞相面前脱身。”
郭英的阿姐是齐元兴妾室,为避婚约,孟开平思来想去,最终求到了郭夫人那儿。
“嗐,这有什么好谢的。”郭英摆摆手,无奈道:“我阿姐的话,丞相多少还是愿意一听的。况且你不情愿,婉清她又并不反感嫁给思危,说来倒比配你合宜。”
谢婉清与齐文正已然成婚,如今都随着夫君征战去了。两人和和美美,也算是桩好姻缘。
“唯独杭家这事才算棘手。”
郭英自沏了盏茶,颇为忧虑道:“你从始至终不肯出面,那杭大人未领恩情便罢,反倒处处提防咱们。幸而丞相这会儿没空理会这些,否则,若教他知晓杭大人根本无意出仕,恐怕是再难客客气气礼遇他们一家了。廷徽,莫要嫌为兄多嘴,你何不如与杭家人道明来去缘由呢?莫说平日开销,就连他们住处的赁金都是你出的,何必让我白受他们的谢?你待他们百般庇佑,若说为着那位师姑娘……做到这一步,足算是至情至义了。”
这是郭英的心里话,也是公道话。他眼见着孟开平赎罪似的默默做了这许多,却不敢在杭家人面前露面,实在替他憋屈。
“可是郭兄,我太过亏心了。”
然而孟开平始终迈不过心里的那道坎,他摇摇头,苦笑道:“我见了她舅舅,便会想起她爹娘,想起我是如何像个得志小人一般霸占强迫她。我向来不耻世家高门,可面对杭家,我直不起腰杆。我亏欠她的太多,如今也还不到她身上,便只能尽心替她看顾亲眷了。”
郭英听罢,数次欲言又止,但终究还是把一切劝解的话咽了下去。
“从前我不明白,如今总算明白了。”郭英长叹道:“婉清那样好的姑娘,为何憾不动你的心分毫。世间情缘本就是不讲道理的。”
如果孟开平从未见过师杭,那么,或许娶了谢婉清也能成就相敬如宾的一辈子。可一旦遇见了那个人,和美与否、悬殊多少便皆不要紧了,错过才是最大的遗憾。
“不过除了她母族,师家眼下的形势更似火煎。”郭英好心提点道:“宫中那位淑妃娘娘一旦生下皇子,师家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元帝外戚。倘若真到了兵戈相见那一日,留情则又成全不得忠义二字……廷徽,你要早日思定才好。”
孟开平感激他的关切,认真应了,而后正要谈及赵将军与陈友谅的对战,却骤闻屋外喧闹。
那声音又急又响,还兼有呵斥守卫之语,孟开平细听面色一沉。
是黄珏。
此处未丞相府邸,机密甚重,若无天大的事绝没人敢如此造次。两人正要起身赶去,却见黄珏已然大步穿过了回廊。
“孟开平!”
他的身影在窗前一闪而过,下一瞬,他便一把推开门,直直与孟开平与郭英对上。
孟开平见黄珏从来都是神气十足的倨傲模样,从未有过如此失魂落魄之态。此刻,他的右手还紧攥着马鞭,面容憔悴,神情恍惚,整个人风尘仆仆至极,也不知昼夜不停赶了几日。郭英见状同样暗道不好,一颗心立时悬了起来。
“不好了,出事了……”
黄珏哑声开口,很快却哽咽住,细看竟是眼角泛红。
他望着孟开平,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道:“太平府被陈友谅攻陷,花云将军宁死不降,守城八日,战死……”
“太平府人马全军覆没……没救了,咱们已经回援不及了。”
——————————
—————
喜欢是索求,而爱是终觉亏欠。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